 我爱山大,不仅因为山大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而且她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爱山大,不仅因为山大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而且她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从大学毕业,倏忽之间已过四十年,正如古人说的光阴似箭如白驹过隙。而今我们班最年轻的同学大概也快到退休的站点了吧?只是就自己而言,只是虚度了春花秋月,却没有多少可足道的经历和事迹。从这一点上说,自己的心中一直存着羞与人说的愧色。看了同学们取得的业绩和功成名就的事业,衷心地祝贺,当然也与有荣焉。固然,平平淡淡亦是生活,总有一点深思可以写下,权当此生中的一个合式的小结!
回看中国现代的发展历史,七七年正是黄金岁月的开始,我们有幸在高考改革的首年被大学招唤,相聚于山东的最高学府。说真的,我那时并不明白时代的意义,更不能知道这是中国改革开放黄金四十年的伊始。
入学报到并不是我第一次来济南,大概是1976年夏,我曾因工作来过,那时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山东煤炭招待所,完成了社调任务后,去英雄山、黑虎泉边的护城河看了一遭,那个时候还没有解放阁的阁,当然也看不到护城河的墙。恰好那几天阴雨绵绵,我便以为济南是潮湿多雨的城市。但我不知道山东大学在哪里?毕竟是大省城啊,相比家乡灰土土的煤城,那是不得了的鲜亮,繁荣。我问一起来的领导是不是到过山东大学,他说看过,大门很朴素,路边的树修剪得很特别。后来我知道他说的一定是洪楼校区的西门。这是我对山大最早的所知。我也给自己下了一个虚幻的梦想--来这里上大学,那个时候高考还没改革,想上大学靠推荐,那不是普通百姓能圆的梦,其原因你懂得!1977年“轰”得一声巨响,高考招生改革了!我的梦总有可能实现了,三个志愿我报的前两个都是山东大学。

为啥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系?其实那个时候也不大懂别的专业。只是在高中的时候,政治课老师讲得一堂很精彩的《实践论》,高中的一个大龄同学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手中不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也传着看过几篇,很是可读有趣。我的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因为煤矿事故离世的,我到了十八岁,高中还差一个学期就顶替父亲去矿上工作了,被分配到子弟学校,教了一年小学,然后在总校做行政秘书,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这个阶段对哲学发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周末有时间,就去市图书馆阅读,那个阶段,除了读一些文学名著之外,很多时间都花在历史上,对了,那个时候只能借阅到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他把中国的哲学史写成了儒法斗争史。历史阅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一些古文选。我知道山东最好的大学是山东大学,我最了解的学科是哲学,因此,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山东大学哲学系。第二志愿是中文系,第三志愿是啥已经忘了。我入学的那一年21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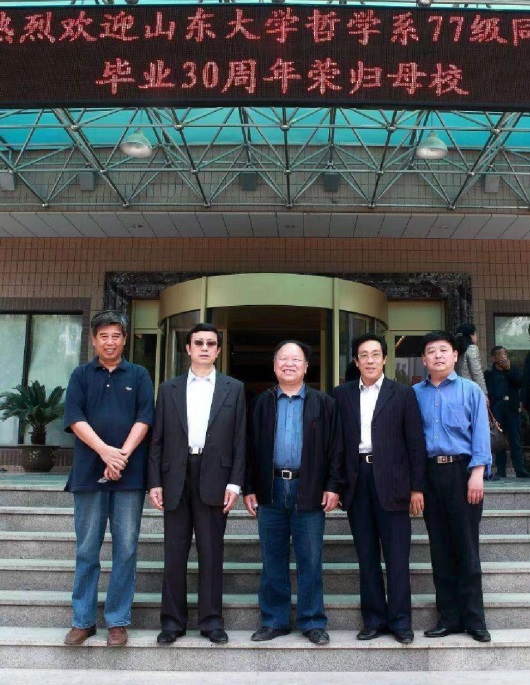
我报到的第一天,从火车站出来,坐上学校的接站车,一直被拉到新校,也就是后来的中心校区。一个十分开放的校园,有校门却没有完全的围墙,西北角是一片菜地,东面是一片田园风景的麦田。校园里的树参差不齐,有的合抱那么粗,有的还是柔弱的树苗。第二天早晨,济南的早春还没有从冬天中醒来,冷冷的,地上有一层薄薄的雪,薄的像霜一样。我出北门想看一看那个古朴的大门和路边美丽的树,却什么都没有看到。大概顺着路向东走到一个药厂的附近就回来了,因为冷,也因为不熟悉路。
新生的宿舍区在西北角第一排房的一楼,门口贴着该房间的同学的名字。每个人的床铺位置都排好了。无论宿舍换到什么地方,这个排位都没有变。我在开门的左手下铺,正好是门后的位置,和我对位的下铺是孔令芝,而今他已因病作古好多年了。孔的上铺是刘玉安。门右手南侧是班长李宏祥和王国庆,左手南侧是袁文颇和孙恒志。恒志兄是体育委员,负责早晨跑操,他和班长比较年长,像大哥哥一样爱护我们。我的上铺一开始好像是没有人,后来七八级的刘陆鹏住过一段时间,再后来就是赵瑞林同学,但他在别的组。
刘玉安是胶东人,乡音比较重,所以我的印象比较深刻。一开始听他的话就像听外语。他进门第一句话说:“我还以为自己走错儿了地方,到了女生宿舍呢”?这是因为老孔和我的名字语音上的确有些阴性化特征,其实我的“岭”字还是阳性的成分大,老孔的“芝”字确实容易误解。玉安是我们的组长,一直都是最勤快最操心的人。
文颇弟是否还记得在班级文艺活动会上你朗诵我写的一首粗糙的诗,字正腔圆。还有于炳贵兄的现场俄语翻译,相信不少人都被你们镇住了。
当然,肖连生的温文尔雅,王国庆的睿智,还有吕敏和王毅平的贤淑,都给我们组增添了难以忘怀的魅力。
有人说,上大学不住集体宿舍不仅仅是一种遗憾而且是巨大的损失。这话不假,我们很多人生的经验和知识都是在宿舍的争论中进步的。当然,恒志兄睡午觉一年四季都不盖东西,这得益于他多年的军人训练。班长每周从家回来都会像闹钟一样准时,这些生动的细节令我永远难忘。
新生入学之后就是军训,一开始是在文史楼北面的球场上练习正步,我们和数学系的同学同在一个场地,他们人多,花枝招展的成为一道风景,我们哲学系的同学,基本上都是青衣青裤,即使是班里的女生也没有花色的服装,灰色是那个时期的典型特征,据说外语系的学生是例外。如果说中文系是我们山大的天之骄子,外文系就是天之娇女了。不过外文系在老校,除了大集会很少见到他们。
山大的新校和老校相隔着一个历城县,如果步行需要好大的一段时间。第一次的新生大会我们就这么走过去,每人提着一个马扎子,排着长长的队伍迤逦而行,会议大厅在西门边洪家楼大教堂的对面,非常简单朴素,后来在这地皮上改建成山大附中了。孙汉卿书记,吴富恒校长和教务长(好像姓赵)做了很精彩的报告,鼓舞人心的话都忘记了,但有两个事情仍然记忆犹新,一个是教务长说的一段打油诗:“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本好过年。”另一个是书记或校长对山大历史的回顾中,谈到校领导的风采时说,华岗的哲学讲座和成仿吾的政治报告,那是国内风靡一时的新潮,因此而造就了那个五、六十年代山大的辉煌。我后来专门查阅了五十年代的《文史哲》,的确有很多华岗讲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文章,这本享誉中外的学术杂志就是这个时期华岗创办的。
大一是最难忘怀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一。有很多事一直像电影一样留在脑海里,选几件说说吧:一个是午夜的“铃”声,宿舍外面靠着半截围墙和菜园子的是一条马路,凌晨进城的菜农大概车子上挂着铜铃,“叮叮当当”的声音时隐时显,我总感觉自己在做梦,静静地听着,听着,又睡着了。二是樊瑞平老师的辩证唯物主义课,樊老师讲课简洁、生动,智慧。他说宇宙是无限的,从黑板的一边比划到另一边,如果说宇宙是有限的,那么宇宙之外是什么?就如这黑板的边外是什么?毫不怀疑物质的世界之外仍然是物质的世界。当然,宇宙的无限性是需要科学来证明的,樊老师形象的解释告诉我们什么是时间、空间、运动等等。哎,说实话,我而今虽然知道什么是宇宙的无限性,但对于“无限”这个东西仍有很多的疑虑。三是半拉子图书馆的东边就是一派农田,在春末夏初,麦黄未收时节,济南的夏天很是闷热,大大的太阳落地之后,樊老师和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徐教授摇着芭蕉扇,在麦田的小路上边乘凉边说些什么。那个时候最热闹的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同学们边走边议论,很有一点逍遥学派的风格。四是在文史楼的北楼一层参观山大的电子计算机,满屋子的机器零件,还有靠打孔输入的设备,显示“欢迎”字样的显示器。回想起来,这个东西其实是最有意义的新玩意,只是当时我很难意识到这一点。五是学术讲座特别多,特别是中文系和历史系,从诗圣,红楼梦研究到民国历史,从朦胧诗到李清照,大凡有讲座我都要去听,也确实受益匪浅。在大一,许老师的历史唯物主义课也非常精彩,许老师阅历丰富,语言犀利,能说也敢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和樊老师风格截然不同。
我记忆中一年级的山大,图书馆很小,在文史楼西边的拐角里,对面的平房是阅览室和教师的参考室。学校的东边没有围墙。我们集体到食堂打饭,我们排队去水房打水,我们步行去洪家楼老校开运动会,听领导们的报告。我们上课分小组讨论,我们晚上熄灯了还会学术争论,我们周末在大操场看露天电影。我呢也经常去阅览室去看报纸、看大参考,还有一些珍藏版的书籍。在大学时代,大一的生活满满的,即使是放假也要带几本书回家,不过又几乎原封不动的带回来,后来就不再这么傻了。

大学四年读了20多门课程,有本系的也有外系的。中哲史,西哲史,逻辑学,还有美学等都是我最喜欢的课。我们班50多位同学,职业和年龄差别都比较大,虽然生活的阅历不同,但大家互相关心,其乐融融的氛围始终如一,这要归功于宏祥班长和昌平书记等大哥哥们领导有方,和谐一致,归功于同学们的团结和理解。大学的生活有欢乐有伤心,有希望有遗憾。同情同理,人生就是如此吧。
我和多数同学不同的是,毕业后仍在山大。咱们那个时候大学毕业都是国家分配工作的,大家虽然都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但方案一公布,也都知道适合自己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要求条件,我自己知道大概被留校了。在这段纷纷嚷嚷的时间,我主要是在图书馆看书。我感谢辅导员张平老师把我划分到9个留校的同学中。从此,我一直在这里工作直到下车的站点。
在这四十年里比较简单、平平淡淡。但也有几个时间点。留校初跟着聂风峻老师给经济系的哲学课助教辅导,后两年给数学系和化学系上哲学公共课,1984年学校放开了考研限制,我和其他留校的几个同学报考了在职硕士研究生,不幸的是查体出现了乙肝病毒感染,不得不休假养病。前前后后接近十年时间才痊愈,这段期间,非常感谢张立勇同学专门来探视。殷殷之情,至今萦怀。当然也非常感谢有德的友情和照顾,不然我也很可能随着老孔而去。大概是1986年学院调整,我跟金守臣老师一起弄符号逻辑。这一段时期,系内有5个人从事逻辑教学和研究,于惠棠老师、梁泉英老师在传统逻辑和辩证逻辑方向,金守臣老师、吴东民和我在现代逻辑研究方向。系外庄平同学在社会学系教传统形式逻辑,后来她写了一本逻辑教材送给我,我给她写了一篇评论。回想在大学期间,她任《哲学笔记》的原著课代表时,我们曾就列宁书中“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有过深入的讨论,她对我写的课后作业深表赞赏。只可惜她英年早逝。因于我自身病困的感受,对她的不幸去世尤其伤感。2007年2月22日,我为她写了一首怀念诗:
《凋落的海棠花》
我用这首诗写下我对同学的哀思
春天来临的时候
海棠花开了,又谢了
伴着花儿的凋落
我们为你送别
那是悲伤地,永远地送别……
在严寒过去之后
我们有缘聚会在春天的校园
在黄绿色的枝叶间
开了的油菜花是那么灿灿
嗅着雨后校园清新的空气
有几株柳树曳摇在我们课堂的窗前
我凝视着天上的白云
白云分了又合合了又散
只记得麦田在我们身边一次次变色
小树林的枯叶一次次零落
那群在树梢上盘旋的暮鸦
似乎还在那里呜唱着哀歌
在这段时间,我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存在还是发展”的问题。后来金老师去了青岛大学,于老师退休,我和梁老师做了个计划准备在语义逻辑方面作一点探索,因为她去国外进修就是这个方向,还送给我一本这方面的文集,不料天有不测之风云,我假期回来后就听说梁老师病故了,她还是那么年轻啊。符号逻辑在大学虽然学过一点,金老师教的,也不过是一点常识,但真去开课难度不小,我花了接近六年的时间边学边教。有时间就去数学系听数理逻辑课,参加过国内的专业培训,这个阶段从行内来说对现代逻辑搞得也算挺热。没有适合的教材我就自己编写。简单地说,现代逻辑的内容相当成熟,虽然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金岳霖就开始把罗素的逻辑理论介绍到国内来,也有北大王宪均,南京大学莫绍揆等大家学者从事研究,他们主要分布在数学学科。但改革开放前数十年国内完全忽视了现代逻辑的教学和研究是一个事实,所以,开放之后突然火爆起来,但师、资都非常贫乏。爬过这段坎之后,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才发现这是一条多么艰难的路,没有扎实的数学基础,这条道越走越难。像美国的王浩后期也从逻辑研究转到对哥德尔后期的哲学思想研究。从弗雷格、罗素到哥德尔,前人的成果像大山一样摆在那里,只是浏览就需要毕生的心智能力了。大家明白,数学的东西,会就是会,不会就立时卡壳。我记得有一次证明元逻辑的完备性定理,写了两黑板,突然就论证不下去了,卡住了。听懂的学生也不多,就只好留给下一堂课了。搞现代逻辑的人,基本都需要做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冷板凳,即使这样也很难搞出名堂来,天才毕竟是极少数人。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也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那段时间,在我的母亲病故的那些日子,我深刻反省了自己近十年的学习研究和生活,认识到现代逻辑并不是我能够行得通的道路,毕竟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阶段,欠缺的基础知识是无法回避的。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比较适合应用的方向走一走。但是对于教学是没有问题的。这种研究和教学的“精神分裂”,一直令我十分痛苦。
不少熟人说做学问不应该选逻辑这样的方向,毕竟几百年才有那么一点进步,事实确实如此。不过我自己明白为什么走这条道,“存在还是发展”对我一直都是问题。现代逻辑虽难,过了坎就无需再去翻找资料,这对我很适宜。因而到了90年代中期,我感觉逻辑的方向无法再搞下去了,教学尚可以继续,但科研肯定搞不出名堂来,除非发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文字混混日子,这是我非常不愿意做的事情。于是转到认知的方面,这个东西国内厦门大学做得比较好,海外就是芬兰学派了,我写过一点东西发在校刊上,由于研究的资料太少,也就不了了之了。在余下的一些时间,我仅对感兴趣的东西做了一些研究,这些东西不说也罢。几十年的工作,断断续续也研究了不少资料,留下了一些思考。回过头来仔细推敲整理,或许对后来者有一些启发的意义,这是我现在一直做的事情。人生若逆旅,都是路行人,或许这是我今后最大的寄托了!
总之,毕业四十年,我在山大四十年,零零总总的原因,一直没有离开母校,我看着山大成长,看着山大发展,而今,我们这一代已经老了。
试想,假如个体的生命是无限的,人生终究会没有滋味,假如心中存着无法消弭的遗憾,那不过因为人们不可能彻头彻尾地觉悟。所以西方才有谚语说:“我们总是老得太快,聪明得太迟。”
“77级”是一个符号,一个永远的符号,因为她是一个时代的开端,也因为她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
文:马士岭
图:马士岭、《如歌岁月》编辑组

